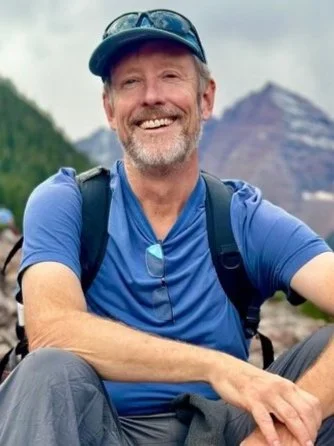慈善事業與款待
托德·布雷福格爾 (Todd Breyfogle) 博士
阿斯彭研究所 (Aspen Institute)人文研究與實踐資深顧問
陌生人來到門口,被邀請進來。主人說:「來和我們一起吃飯吧。」主人和陌生人一起進餐,滋養身體,提供安全和休息。用餐期間或許還會有交談,但只有在用餐結束後,陌生人才會收到最親密的邀請:“告訴我們你是誰,以及是哪些故事成就了你。”
這是一個極其不可思議的故事。陌生人被邀請進來,卻一無所知,也未經考驗。用餐的親密感先於身分認同和經驗的親密感。陌生人自然的被了解,其次才透過名字和社會習俗被了解。食物和休息的禮物是無條件提供的。
在我們現代人看來,這確實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故事,然而在荷馬 (Homer) 的敘述中,它卻反覆出現奧德修斯的故事。這個看似不可能的故事並非虛構,而是許多古今文化中普遍存在的習俗,在這些文化中,待客之道至關重要。
這種義務的根源在於宗教。在希臘人和亞伯拉罕傳統中,陌生人可能是化身為神或天使的化身。耶穌曾說:「我實在告訴你們,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,就是做在我身上了。」 待客之道作為一種虔誠,承認了所有人類都擁有神一般的潛能。對孔子而言,待客之道源自於互惠原則,即待人如己。 「在外要如同有貴賓在場般的舉止得禮,對待平民百姓,應當如同主持祭祀一般慎重。」 即使出門在外,互惠原則也要求我們成為主人,並以對生命的宗教敬畏和祭祀的慶祝之情來對待他們。
這些根植於虔誠和互惠的待客之道之所以難以實現,是因為它們顛覆了我們現代經驗的邏輯。按照現代邏輯,告訴我你是誰,你想要什麼,然後我再決定要給你什麼。現代邏輯始於自我;而待客之道的邏輯則始於他人。事實上,待客之道的根源並非我們自己的力量和安全感,而是我們眼前之人的匱乏、脆弱和人性。
待客之道的難以實現蘊含著深刻的意義。共同用餐——不同於單純提供食物——是一種親密關係的形式,它不僅承認我們共同的生活,也承認我們共同的人性。共同進餐不僅是身體上的滋養,更是精神上的溝通。因此,奧德賽 (Odysseu) 的故事——所有關於待客之道的故事——強調了我們有機會分享的物質和精神禮物的不可分割性。
首先,在提供共同的餐點時,主人提供的是社群和交流。共餐承認脆弱性既是物質的,也是道德的。陌生人——作為陌生人——從定義上來說,是暫時(或許是永久地)脫離社群的。提供食物在物質上是必需的,但在道德上是不夠的。食物是物質生活的必需品;一餐是人類生存的必需品,也是充分的。其次,主人邀請的是真情實感,而非表演。款待的順序至關重要。提供餐點是無條件的;它無需證明會員資格或交易價值。 「先吃後說」意味著客人不必「為他的晚餐唱歌」。餐後,客人和主人在共同進餐之後,彼此的認同和自我揭露會更加真誠。第三,物質和道德禮物的結合,既體現了信任的紐帶,也增強了信任的紐帶,而信任對任何社群都至關重要——信任彼此,也信任在個人的脆弱得到關注時對自己的信任。
共進晚餐、誠實、信任——這些才是共進晚餐的真正成果。款待的義務始於物質需求,但並非止於此。事實上,在共進晚餐中,在款待的邏輯中,我們的物質需求和道德需求是密不可分的。正如亞里斯多德 (Aristotle) 提醒我們的那樣,社群始於生活的物質需求,但它的滿足感體現在人與人之間團結互助的歸屬感中,而友誼是這種歸屬感的最高形式。
我們現代物質盈餘計畫的成功——無論分配多麼不均——掩蓋了我們的需求既是道德的,也是物質的。慈善事業的教訓意義重大,因為慈善事業主要關注物質變化往往顯而易見的影響。而我們共同生活中更深層、更持久、更人性化的道德和精神層面,則不那麼明顯,也更難衡量。
慈善事業的邏輯,以及一般的社會行動,都應該從款待的邏輯中汲取有益的教訓。當我們奉獻自己的物品時,我們奉獻的是物質;當我們奉獻自己時,我們奉獻的是精神。當我們共同分享一頓飯的滋養,以及關於我們是誰的滋養對話時,我們既付出,也接受,展現了人性的完整性。在分享一頓飯的過程中,我們在滿足物質需求的同時,也拓展了道德生態。無論是主人還是客人,當我們分享一頓飯時,我們都會成為更好的人,成為我們被召喚成為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