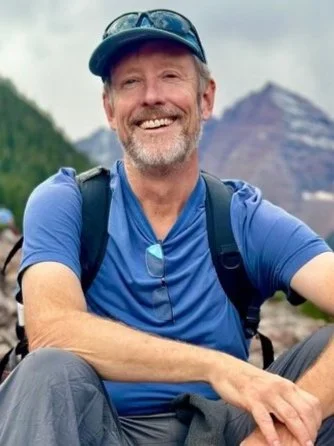慈善事业与款待
托德·布雷福格尔 (Todd Breyfogle) 博士
阿斯彭研究所 (Aspen Institute)人文研究与实践资深顾问
陌生人来到门口,被邀请进来。主人说:「来和我们一起吃饭吧。」主人和陌生人一起进餐,滋养身体,提供安全和休息。用餐期间或许还会有交谈,但只有在用餐结束后,陌生人才会收到最亲密的邀请:“告诉我们你是谁,以及是哪些故事成就了你。”
这是一个极其不可思议的故事。陌生人被邀请进来,却一无所知,也未经考验。用餐的亲密感先于身分认同和经验的亲密感。陌生人自然的被了解,其次才透过名字和社会习俗被了解。食物和休息的礼物是无条件提供的。
在我们现代人看来,这确实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,然而在荷马 (Homer) 的叙述中,它却反覆出现奥德修斯的故事。这个看似不可能的故事并非虚构,而是许多古今文化中普遍存在的习俗,在这些文化中,待客之道至关重要。
这种义务的根源在于宗教。在希腊人和亚伯拉罕传统中,陌生人可能是化身为神或天使的化身。耶稣曾说:「我实在告诉你们,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,就是做在我身上了。」 待客之道作为一种虔诚,承认了所有人类都拥有神一般的潜能。对孔子而言,待客之道源自于互惠原则,即待人如己。 「在外要如同有贵宾在场般的举止得礼,对待平民百姓,应当如同主持祭祀一般慎重。」 即使出门在外,互惠原则也要求我们成为主人,并以对生命的宗教敬畏和祭祀的庆祝之情来对待他们。
这些根植于虔诚和互惠的待客之道之所以难以实现,是因为它们颠覆了我们现代经验的逻辑。按照现代逻辑,告诉我你是谁,你想要什么,然后我再决定要给你什么。现代逻辑始于自我;而待客之道的逻辑则始于他人。事实上,待客之道的根源并非我们自己的力量和安全感,而是我们眼前之人的匮乏、脆弱和人性。
待客之道的难以实现蕴含着深刻的意义。共同用餐——不同于单纯提供食物——是一种亲密关系的形式,它不仅承认我们共同的生活,也承认我们共同的人性。共同进餐不仅是身体上的滋养,更是精神上的沟通。因此,奥德赛 (Odysseu) 的故事——所有关于待客之道的故事——强调了我们有机会分享的物质和精神礼物的不可分割性。
首先,在提供共同的餐点时,主人提供的是社群和交流。共餐承认脆弱性既是物质的,也是道德的。陌生人——作为陌生人——从定义上来说,是暂时(或许是永久地)脱离社群的。提供食物在物质上是必需的,但在道德上是不够的。食物是物质生活的必需品;一餐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,也是充分的。其次,主人邀请的是真情实感,而非表演。款待的顺序至关重要。提供餐点是无条件的;它无需证明会员资格或交易价值。 「先吃后说」意味着客人不必「为他的晚餐唱歌」。餐后,客人和主人在共同进餐之后,彼此的认同和自我揭露会更加真诚。第三,物质和道德礼物的结合,既体现了信任的纽带,也增强了信任的纽带,而信任对任何社群都至关重要——信任彼此,也信任在个人的脆弱得到关注时对自己的信任。
共进晚餐、诚实、信任——这些才是共进晚餐的真正成果。款待的义务始于物质需求,但并非止于此。事实上,在共进晚餐中,在款待的逻辑中,我们的物质需求和道德需求是密不可分的。正如亚里斯多德 (Aristotle) 提醒我们的那样,社群始于生活的物质需求,但它的满足感体现在人与人之间团结互助的归属感中,而友谊是这种归属感的最高形式。
我们现代物质盈余计画的成功——无论分配多么不均——掩盖了我们的需求既是道德的,也是物质的。慈善事业的教训意义重大,因为慈善事业主要关注物质变化往往显而易见的影响。而我们共同生活中更深层、更持久、更人性化的道德和精神层面,则不那么明显,也更难衡量。
慈善事业的逻辑,以及一般的社会行动,都应该从款待的逻辑中汲取有益的教训。当我们奉献自己的物品时,我们奉献的是物质;当我们奉献自己时,我们奉献的是精神。当我们共同分享一顿饭的滋养,以及关于我们是谁的滋养对话时,我们既付出,也接受,展现了人性的完整性。在分享一顿饭的过程中,我们在满足物质需求的同时,也拓展了道德生态。无论是主人还是客人,当我们分享一顿饭时,我们都会成为更好的人,成为我们被召唤成为的人。